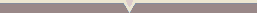赛珍珠纪念馆游记
江苏大学附属学校初二学生 王佳怡
仲夏的镇江,西津渡古街的青石板地仿佛也被热浪点燃,每一寸都散发着江南夏日独有的炽热气息,蝉鸣裹着热浪,却在拐进巷弄的瞬间被隔绝。赛珍珠纪念馆的朱漆门扉半掩,门檐下悬挂的铜铃轻晃,似在邀约游人走进一段交织着东方烟火的岁月。
踏入院中,最先撞进眼帘的是那方青石板天井。阳光透过紫藤架的缝隙,在地面织就斑驳的光影,细碎的紫花落在石板,像撒了把碎星。这青石板,据说是当年,赛珍珠常与保姆“王妈妈”坐着纳凉的地方——讲解员轻声道,她就是在这里听王妈妈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学唱镇江童谣,连后来写《大地》时,笔下农家院的石板路,都带着这里的温度。我俯身轻触石板,指尖仍能触到余温,仿佛百年前的笑语还藏在石缝里。
展厅的第一处展柜,静静躺着一本泛黄的线装《论语》,书页边缘被摩挲得发毛,空白处有稚嫩的铅笔批注,是中英混杂的字迹——“仁,就是对人好。”“这是塞珍珠十岁时的读本,那时她一边跟着父亲学英语,一边听王妈妈用方言解读古籍,两种语言在书页间碰撞,悄悄埋下了跨文化理解的种子。旁边的老照片里,少女赛珍珠捧着的正是这本《论语》,眼神里满是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亲近。
再往里走,“文学成就”展区灯光渐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复刻奖牌在展柜中泛着柔光。奖牌旁,《大地》的不同版本堆叠着,从1930年英文初版,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文译本,再到近年精装重印本,书脊上的文字换了又换,不变的是封面上那片厚重的黄土——那是赛珍珠记忆里镇江田野的颜色,是她笔下农民王龙赖以生存的土地。我驻足在一本1937年的译本前,扉页上有读者的旧字迹:“从这本书里,我看见了自己的家乡。”忽然懂得,《大地》之所以能跨越国界,正因它写的是人类共同的对土地的眷恋。
展厅尽头是落地窗,框住了一幅古今交融的画面:远处的金山寺的塔尖在阳光下闪着光,近处古街的黛瓦与现代高楼相映。这里陈列着赛珍珠晚年的书信,信纸已经泛黄,字迹却依旧工整,她在信里问友人:西津渡的石板路还在吗?王妈妈的后人还好吗?”字句间满是对镇江的牵挂,这份牵挂,让她虽远在异国,却始终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待离开时,暮色已漫过古街,紫藤花在晚风里轻轻摇曳,回望纪念馆的朱漆门,忽而就懂了,这里不只是一座陈列往事的建筑,更是一座跨越山海的桥梁——它连接着赛珍珠与镇江的温情。让每一个来访的人,都能在旧物文字里,触摸到那份穿越百年依然炽热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