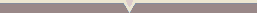中国方面关于我们作品的意见,无论怎样地主观,我总是很有兴味,而且无论怎样,我总是予以很诚恳的同情。现在对于江教授的几点,我也抱着 同样的诚意。
在第一点,我认为江教授所说,对于一个中国人的描画,它不仅仅是平常的写照,而且不像那些在盖棺定论之前总是不完成的写真。这话是非常地正确。无论是谁,他如果要想弄明白那些写真,他一定要去体验实际生活的真实性。坐位的姿势,褶纹,郑重的态度,静止的容颜,官衔的顶子。我所注意的在光线怎样?和阴影怎样?但或许我有意省略了那“官衔的纽扣”,我假如他能够认出这是他自己,那我就不必管他让他在画上提出这“官衔的顶子”问题!我只是画我印象中的他,我自然不必辩解。
但最好我还是就江教授原文的结尾,来讨论几个小点。依着原来的次序,尽量简短地说说。
《东风。西风》中的这种事,即那个上吊的少妇被人割断带子解救下来的事,我是亲身经历了的。因为她是我的挚友,我很明了她的困难,她上吊不久就被救放下来,而且立即请了许多和尚希望召回的灵魂复归到她还有温度的身体里。一字一字的,那故事完全出于我的生活经验。
这老母亲,确是丢掉了《易经》。照例我也晓得圣书是不可以丢的,但是我又弃置了“官衔的顶子”。我曾看到一个疲弱而忧郁的妇人,捧着一本圣书,让它从失掉神经作用的手指中间,堕落在地板上,正像我在家里看见一个革命军士把我的一本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撕成片片。
在《大地》一书中我所取的地方背景,那里茶叶是很希罕的,很少几片茶叶浮在开水的面上,这情形,我看到过好几百次。
回人所在牛肉为普遍的食物,因回教徒不食猪肉,而回人又散处各地,故我从未经历某一地域,于牛肉的获得如何难于猪肉者,无论何处往往成为极普遍的食物,与猪肉同供佐膳。当然贫穷的人不能多得肉食,但值假期佳节,一碗肉圆与一碗牛肉并陈,亦至通常,无庸赘述。屠猪几为日常之事,较大的城镇,且日宰一水牛。我想江教授又注意于“官式之纽扣”,因其谓牛属家畜,忠其所事,不能宰食也。
在我们所居的地方,普通人家生了儿子则分喜蛋,但如生女儿,喜蛋是不会分送的。
月饼因是专用点缀中秋节之用,但在新年及其他佳节,也有混同别种饼饵供奉者,正像在各大城市中年糕除暑天外,无论何时,均可购得。这恰同西方的果饼,或梅子布丁,相沿为季节特制品,但实际上任何时期,都可以吃到。而我呢,宁可疏忽祖传,而趋重事实的。
我曾赴药店里去取药方,当我表示对龙齿怀疑的时候,那店员就坚定地说,“当然,这实在是狗牙齿。”他还示我老虎的心,那是一片烘干扎缚的肉脯。
我曾看到子孙们步行送葬,坐轿送葬,在南京,我还看见他们乘坐马车或汽车来往上坟,在这摩登时代,这“宫样的纽扣”,往往或缺,他们只拣他们所愿意的做。
像《儿子们》一书开头一章所述的情景,我曾很有兴味地注意,一个很老的妇人是我的一个邻舍,她时常确切地告诉我她的儿女们怎样筹划她的葬事,很明显这给予了她极大的安慰。
在我们那地方,为死者每为之预备两具台位,一是临时的,另一块是永久的。这典礼就像我所描写似的。因为我末敢全信我的记亿,当此书尚在草稿时我曾把这一节读给我一个中国朋友听,以求信实。
我须请江教授原谅,有许[多]军事长官,确如王老虎的行为虽无名义上的地位,但实获当地一切的统制。而我于王老虎并未与以名义上的地位。而且假如我愿意我可以把这些强横霸道的人,名之为极类似之中国政府高级人员。理论上说来,这当然不是的,但同样我并不留意于这“官式的纽扣”。
但凡此诸点,均非重要,中国各地习俗大有殊异,无人能留存不变之静态,只能够说“在我所处的区域中见这样的”而已。因此,我只拣选我所最熟知切近的地方,以期至少对某一地域不失其真实性,再加上我曾诵读于该地域中的中国友人之前以求印证。
现在我要谈到较之前面更加有趣的地方了。江教授对我用“Shuei Lake”一字,提出抗议,实则这无非是一部中国伟大小说《水浒》的译名,这只是个词语,告诉西方的读者一个以强盗著称的有名地区。这“Hu”字在英文中实在是没有意义的,这或将近似“Margins”(边缘)一字,但“WaterlyMargins”又怎能传达到西方人的心里?这个可以用英文Swei,Shui, Shue以及江教授目下所加上的“Shuei”等拼音的字,无疑地是“水”。但依我想,江教授用“River”一字来联缀成语,是完全错误,这些著名强盗盘踞之区,决不是一条河,而是濒近叶芦掩映的大湖,在其中还有许多喽啰啸聚的支流水道。
然要研讨中国词语之如何译成英文,并非数语能尽。《水浒》之译音在我采用最简单之形式“Shuei Hu”,但无疑地我不能希望江教授之完全赞同。我曾以此译名争询其他中国人之意,我也未能自信其判断。
但较此更有兴趣者,即江教授在函中表示的观察,虽系个人的意见,似无关重要。但此点为我所熟知,且每引以为怅者,彼谓“他们(意即指普通的中国平民)或为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实未必足以代表中国人民”。则我只有这样问他,倘若在任何国家内,居大多数者不能为代表,则谁复能代表?
然而我晓得江教授及其他类似江教授者,颇愿以极少一部分的智识阶级来代表全部中国人民。且愿以地大物博庄严愉快的中国人民生活借悠远之历史古画及经典文学以为表现。此诚足实,且为中国文化之一部,但也只成为“官衔的顶子”而已。因为人们是否将忽视一般普遍多数的中国人民,在多灾多难的天时中,在内战频仍的政府下面,在少数特殊阶级的智识分子统辖内还过着健壮的生活,以真理言,我是永难赞同的。
我对于这类的态度,我曾有无限的经验,而今不觉又在江教授函中宣示。过去在对付工人的残暴行为中,在欺凌朴质无文的农夫中,在对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忽视中,我已认识其宣示,那就是世上平民在其国内军事的智识的领袖之下,鲜有忍受更深的痛苦中国人者,中国平民与知识阶级间的鸿沟太可伯了,已成为互不相通的深渊。我曾和平民相处很久,过去十五年中又生活于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因之我晓得所说不致失当。
江教授显露此种态度,可证其对于平民的欠缺了解。他时常侮蔑地说“苦力”和“阿妈”,如果他了解“苦力”的话,他应该明白对于他们,这是个刺激的名字。“阿妈”也是的,仅为一奴仆的专词。在我童年的家庭里,我们的园丁是一个农人,但我们对他都很尊敬,我们决不许叫他“苦力”,就是现在我的家庭里,我也不许孩子们用这名词。我们的乳母,也从没有叫她为“阿妈”(Ama Amah),而时常称之为保姆(Foster—mother)。而她所教诉我们的,无非是良善,我们热忱地爱她,像母亲一样地服从她。虽然她是个村妇,即或她的生命意识不免殊异,她的常识有限,非我所问,但在我,她只是我的保姆而已。现今在我家庭里,我们的孩子也很敬爱异国的妇人,他们称她亦非“阿妈”,同我一样地[用]那个很亲密的老名词。因是这妇人不仅是一女佣,而且是我们忠诚的朋友,孩子们真实的抚育者。我对她决没有像江教授那样的感觉。
这一点似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不能把握者,即他们应以其大多数平民的夸耀,大多数的平民才是中国的生力、中国的光荣。西方人现已不致被骗,而认中国人民一似古旧的写真,这时期业已过去。新闻纸及旅行,将中国的匪患、灾荒,及内战尽情揭露,假使不循我对过去十五年间的回忆,像《儿子们》里的事态也是没有。在全画面中可为减轻者,只赖于平民所具有的性质,他们担负着这祟高的使命,去改易他们的时代。
而这些平民,正如那些无知的知识阶级所掩藏。两三年前欧洲某国的王子,来访中国某城市,因此中国的知识阶级的统治者,恐其看到贫民茅棚,引以为辱,因此用席子造一墙壁,王子的汽车在席墙旁驰过,终无所见。因而我联及到这一点,我作函投一中国刊物,反对这类虚伪的耻辱,因为在此席墙背后,终必不能欺瞒别人者,还是中国民众的忍耐、俭约、勤劳等这些优秀的品质。
但我很引以为怅者,我不愿涉及江教授所指控我书中猥亵之处。最偏狭的宣教师派,会赞同他的话,但我想这种对平常性生活的惧怕张皇,只是某种训练的结果,我不很知道,我只是依着我所见所闻的写述而已。
至于在我的著述中是否能替中国有所效力,只有时间可以答复。我接到许多的信件,他们告诉我读了我这些书,才开始对中国发生兴味,现在中国人对他们已有人性,而别的人已祖此为注释。在我自己,并未存有使命或作何从服新的意念。我写,只凭我的天性要这样做,而我也只能凭我所知道的写,我所知道的又只限于中国,为我所时常住居的地方,我很少同种的朋友,几无一个较为亲密,因此我只写我所知道的人。我最爱中国的人民,和他们同在一起生活,那些人不会留意到“官衔的顶子”的。
【注】赛珍珠对江亢虎评论的答复原刊在New York Times Book ,由庄心在译为中文发表在(上海)《茅盾月刊》(1933年)第2卷第1期,参见本集庄心在的文章《布克夫人及其作品》。